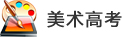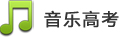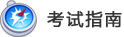| 沈必晟:改革开放以来,您以《大河寻源》起始的系列作品,在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美术评论界对您的界定很多,有的称为“革新派”、有的称作“气势派”、有的把您叫作中国山水画在20世纪里的第四度变革的人,从您个 沈必晟:改革开放以来,您以《大河寻源》起始的系列作品,在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美术评论界对您的界定很多,有的称为“革新派”、有的称作“气势派”、有的把您叫作中国山水画在20世纪里的第四度变革的人,从您个人来看,您觉得哪一种评价最为准确? 周韶华:“革新派”,刘国松常这样提,“气势派”的说法是邵大箴先生首倡的,至于你说的“中国山水画在20世纪里的第四度变革”,则是刘曦林在他的《周韶华简论》中提出的。其实这些说法,我并不太看重,这毕竟是理论家、批评家的具体工作,作为一个以创作为主导的山水画家,我更看重的美术创作。如果硬要我把我的工作思路理一理的话,我以为就这两个字——“创新”。 沈必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您很注重创造性思维在艺术活动中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关于“创新”的解释,譬如把“新奇”、“怪异”作为艺术创作中“创新”的代名词,以为只要不同于别人就可以叫“创新”,有的甚至搞得很“暴力”、“血腥”,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道德感,不知您怎样认为? 周韶华:不错,你说的那些带“暴力”、“血腥”,还有“色情”的所谓的艺术,的确有很多就是打着“创新”的旗号,这些违背人基本道德观念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时期以来过分鼓吹“自我表现”的结果。它们过份强调创造主体的中心位置而全然忘记了美术是现实的艺术存在,没有看到艺术主体和艺术客体的同一性,并且忽略了艺术创造与艺术接受者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体验与理解,它们是一种亲合同一的关系而不是抛开接受者的纯主观表现。当然,张扬“自我表现”有其合理的成分,比如这当中蕴含有个性解放、人性自由等方面的内容,但把“自我表现”夸大到心物二元的对立立场,则明显地违背了艺术的科学精神。艺术创作实际上是个“自然向人生成”和“人向自然生成”的双向建构过程,这个过程中含有一系列主客体二重性特征,只有达到“物我两忘”的主客体超越状态,真正的为大家认可艺术品才自然而然的生成。 沈必晟:可不可这样理解,“创新”离不开具体情境,但又必须打破陈规陋见,离开一定的“具体情境”。 周韶华:是这样,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新”的也会变成“旧”的,曾被我们突破的,后人肯定还会突破我们。因此,艺术家始终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创新,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新的突破。 沈必晟:我注重到,您是一个以创作为主导的中国山水画家,但在您的艺术生活中,理论也占了相当大的份量,比如您提出了“抱一论”、“全方位观照论”、“隔代遗传论”、“横向移植论”、“三面体结构论”以及“新东方文化形态”、“新的综合与新的分化”一系列概念等等,这些理论的归纳无疑都是对您艺术实践的补充,可不可这样认为,您提出的“隔代遗传”就是对传统的继承,“横向移植”就是对西方的借鉴。 周韶华:对,这是我对“创新”的具体解决方案,即在艺术实践中,必须勾连传统与现代,融合东方西方这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一方面对民族艺术的传统进行传承与扬弃,另一方面要使自身精神素质现代化,不断赋于民族精神以新的内容,体现出更新的时代的特色,这就要不断地占有古典资源和现代资源、东方资源和西方资源,处理好民族性与超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承受两种文化的撞击,将民族文化投射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中去,把横向与纵向两种文化移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把富于创造性和科学规律性统一起来,把大胆引进与守住民族特色统一起来,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在深刻体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上下功夫,这样的艺术新体、新风格和新传统才是有意义的创新。(责任编辑:admin) |